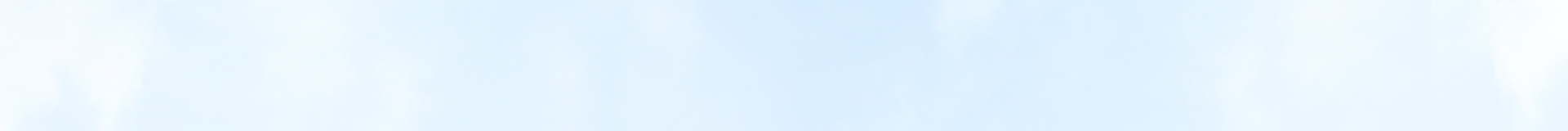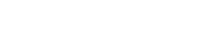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3-12-21 09:32
- 信息来源:随州日报
- 编辑:黄振忠
- 审核:黄振忠
相传大洪山原本大湖山,山上有湖,湖之灵引来两龙,一白一黑。两龙都想占湖为王,一次次地于湖上酣斗厮杀,终于有一天,大湖山经不住它们长年的折腾,顿时山崩地裂,一湖清水尽数倾下,两龙也因水枯而毙,成为樵河古道东西两岸的化石,世代难挪其身。
当年大湖倾泻而下时,多少生灵殁于其中,但定有生还者,他们或居深山打柴,或去绝壁采药,等回到村庄,村庄已夷为平地,千万块大石从山上滚落下来,一条溪谷在乱石丛中弯弯曲曲而行进,而于山侧较缓处,一个新湖明澈如镜,即为落河。
这些少数生还者,带着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悲伤,带着对家园难以割舍的爱,开始将滚落下来的石头一块块搬到高处,堆砌成墙,然后将从乱石间拖回倒下的树为梁,再割下周边的毛草屋顶铺盖。饿了,上山摘些野果;渴了,从溪间捧来清水;累了,枕着溪声而眠……从此,落河就有了新的炊烟新的田地新的生活方式。
曾经大湖安好时,大湖山这边是块极肥沃的盆地。周围的山挡住了冬天的寒流夏天的酷热,是人类理想的生息之地。大湖山崩塌后,从山上滚落的乱石一路覆盖,表层土壤又被湖水冲洗干净,可用土地极其匮乏。为了生存,人们顺溪而下,去低处捕鱼,逆溪而上,去山上砍柴寻宝。踏巨石过溪,越石缝寻路,于是这条由樵夫千辛万苦踏出来的路,便成了今天的樵河古道。
如今樵河古道已焕新。踏着青石板拾级而上,再也不怕迷路,更不会跌倒。所有石级依山就势,虽为现代打造,并不影响其古朴之感,越行越高的石梯就象一条通往仙山的天梯,踏在上面,脚下生风,不免有脱尘追月之感,使你想感叹今夕何夕,良辰美景依依相拥,泉水叮咚琅琅奏乐。
在这条古道上,溪石树是最主要的景观。溪穿石或绕石而行,或急或缓,不慌不忙,郁郁而流,淙淙而去。树贴壁而生,或钻石而出,其形或圆或扁或多角,皆依生存环境而定。有些树烂掉了,从树兜旁发出的新芽又长成参天大树,新树与老树代代相接,使你感到生命的无穷无尽。而这些树,并不是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它们攀着岩石,千万根须被流水冲刷,有时穿过流水插入地下,或者干脆就在岩石上扎根,根一路向下蔓过巨岩,从有限的石缝中钻入地下,又或者,根本就不寻找,直接穿石而过(这只是猜想,因为一块巨石之上并未见根须蔓过,树却从岩上挺拔而起),指向蓝天。
树憎恨石吗?我想不,因为石同样被时间和环境所雕塑。当山崩地裂的那一刻,一些无依无靠的石头滚落而下,滚落时的摔打使它们千疮百孔、肝肠寸断,接着又被自然风化和流水冲刷,它们没有了棱角、没有了位置,它们成不了栋梁之材,只能成为溪中的踏脚石被人踩在脚下。还有一些,它们匆忙脱离母体,落户于陌生的土壤,没有了母体的温暖与兄弟姐妹的呵护,只能坚强地独自站立,成为人依靠的基石。它那么孤独,但孤独中却透着凝重和沧桑,使每一个经过的人感到它的份量和厚实,从而使漂泊的心有了安宁。在离开樵河古道的那天晚上,我就梦到这些站立的石头:当时一群人相约去淘金,走至途中众人无缘无故散去,留下我一人被歹人追杀,为保性命我弃物奔逃,于一陡峭山岩下无路可逃。夕人渐近,心急如焚,不想焦急万分之中,岩上金光一闪,刺得歹人睁不开眼睛……惊魂渐定,一摄像机模样的物件挂在岩石边的树杈上,岩石后转出一人,隐约中轮廓俊美,他轻轻地击打岩的某一部位,岩石缓缓移动,将歹徒隔到岩石的另一边……瞬时眼前便出现一条狭长的山谷,山谷幽深,山花烂熳,溪水叮咚,男子没有说话,手握摄像机向深谷走去,摄像机的画面现在半空中,美轮美奂,无法言语……我内心疑惑男子要去的地方,想跟着看个究竟,却因一点犹豫没有跟上,他身后的路即合上,空中画面也越来越远……醒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梦,它究竟要告诉我什么?当初在那些站立的巨石面,我就被一种什么东西强烈地冲击着,我久久地呆在那儿不想离开,那么梦中一石之隔的两个世界是否就代表了我的现实与人本之间的差距?我们究竟要金子干什么?金子既不能充饥也不能保暖,金子只不过是人吹起的一个泡沫,我们却为它枉费一生心血,而在良辰美景显现之时,我还在犹豫,还不知道去接纳和享受,那么幸福之路又怎么会不在我面前合上呢?
……
写文至此,内心已澎湃难抑,曾经的灾难造就了美丽的樵河,世代的先人踏出了美丽的樵河。千百年来,樵河万物静静地生长、存在,没有言语,它们融进人生的一切哲理,等待着人们去解读去破译,唯独放下浮躁,静默其间,方能识其音容、佳品,用其濡养生命。
那么,樵河曾经的灾难不就成为如今我们所有人的福祗了吗?
那么,我们难道不该接下樵河古道上千万年的足音,让它的声音在世界回荡吗?
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随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是否继续?
您的浏览器版本太低!
为了更好的浏览体验,建议升级您的浏览器!